來源 法律讀庫 微信公眾號
近日,湖南“操場埋尸案”備受社會關注。掩蓋十六年的案件重見天日,十六年來,對于鄧世平而言是黑暗埋沒的十六年,靈魂難安;對于鄧世平的家屬而言是痛苦扎心的十六年,內心不平卻又無處伸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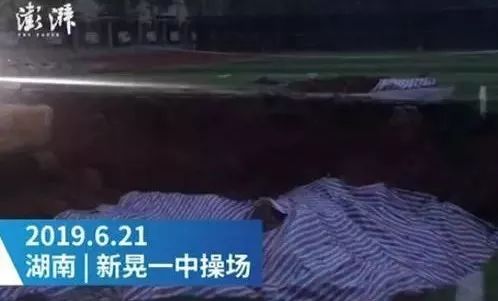
盡管案件尚在辦理之中,但我們可知該案僅僅是冤假錯案的冰山一角,也僅僅是糾正(正在糾正)的冤假錯案的些許倒影。
在今天的法律圈,我們總是會說“正義或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與之相對應的還有一句諺語“遲到的正義非正義”。正義是一個核心范疇明確、邊緣范疇模糊的概念。

《荀子》:“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正義觀念萌于原始人的平等觀,形成于私有財產出現后的社會。而今在倫理學、政治學、法學等領域都被廣泛討論,在倫理學中,正義通常指人們按一定道德標準所應當做的事,也指一種道德評價,即公正。
在刑事司法領域,無辜之人不受冤屈、有罪之人按照法定程序承擔法定罪責即是正義最基本的要求,陳興良教授曾言“司法的最高境界是無冤”,仔細揣摩,現實卻是如此,但不應當如此。
冤家錯案的出現一定是違法的,嚴格依照法定程序查清案件事實,準確適用法律定罪量刑不應當出現個案的非正義,除非法律規定的類罪是非正義的,無冤本為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現實中卻成為一種司法奢侈,成為一種崇高的目標和最高的境界,以致于無限接近而不能至。
每每出現糾正冤假錯案的時候,民眾的司法呼喚異常激烈,既考驗著辦案機關,也考驗律師承辦冤假錯案的能力和勇氣。
為什么公眾這么關注冤假錯案?如何讓人民感受到國家的公平公正,就在于個案的處理結果。大眾迫切想知道真相,卻往往難以獲知真相,在報道的冤假錯案之外,我們無法想象還有多少駭人聽聞的案件存在,我們更無法想象置身案件中的被害者及其家屬的絕望和無助,好奇之余不免心生畏懼,也許自己在未來某個時候也會成為案例中的原型人物。
近些年吸引大眾眼球的冤案屢屢出現,一起起沉睡已久、觸目驚心的刑事案件拉開光明大幕,蒙冤者終于沉冤昭雪、重見天日。每一份無罪判決的背后,都凝聚了法律人的心血和努力。有舍棄尊嚴、丟掉自由乃至生命的當事人,更有勇往無前的刑辯律師,他們堅守著對法治的信仰,對正義的追求,為那些飽受冤屈的人們爭來自由、贏回尊嚴,讓公平正義落到具體的個案之上,維護了司法的神圣和權威。遺憾的是,真正得到糾正的冤假錯案太少,糾正的過程也太艱難。
比如2017年的十大無罪案例:福建寧德繆新華等人故意殺人案;上海丁小紅詐騙案;新疆周遠故意傷害、強制猥褻案;云南盧榮新故意殺人、強奸案;吉林省“孫氏三兄弟”孫寶國、孫寶東、孫寶民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故意殺人案;黑龍江許立華詐騙案;河北邯鄲孔成杰猥褻兒童案;河北滄州楊有軍搶劫案;內蒙古王力軍非法經營案;河北石家莊夏宜榮等三人虛開增值稅發票案。這十起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都是生效判決數年后,經歷種種曲折才啟動再審程序,最終改判。
不單單是這十起案件,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刑事糾錯案件大都如此,如下圖所示:
| 冤案名稱 | 罪??名 | 羈押時間 | 糾錯耗時 | 糾錯主要因素 |
| 譚新善案 | 故意殺人 | 2004.12-2016.8 | 13年 | 長期申訴、高檢抗訴 |
| 陳滿案 | 故意殺人、放火 | 1992.12-2016.2 | 23年 | 長期申訴、高檢抗訴 |
| 聶樹斌案 | 故意殺人、強奸 | 1995.4執行死刑2016.12平反 | 21年 | 真兇再現 |
| 樂平黃志強等五人案 | 故意殺人、強奸 | 2000.5-2016.12 | 16年 | 真兇再現 |
| 呼格吉勒圖案 | 故意殺人 | 1996.6執行死刑2014.12平反 | 18年 | 真兇再現 |
| 黃家光案 | 故意殺人 | 1996.6-2014.9 | 17年 | 同案犯歸案 |
| 高如舉、謝石勇案 | 搶劫、故意殺人 | 2004.1-2014.7 | 10年 | 真兇再現 |
| 浙江蕭山命案 | 搶劫、故意殺人 | 1995.11-2013.7 | 17年 | 真兇再現 |
| 張氏叔侄案 | 強奸、故意殺人 | 2003.5-2013.3 | 9年 | 真兇再現 |
| 于英生案 | 故意殺人 | 1996.12-2013.8 | 16年 | 長期申訴、高檢介入 |
| 念斌案 | 投放危險物質罪 | 2006.8-2014.8 | 8年 | 長期申訴、高院復核 |
| 福清五人爆炸案 | 爆炸罪 | 2001.8-2013.5 | 11年 | 長期信訪、省高院終審 |
| 郝金安案 | 故意殺人 | 1998.1-2007.12 | 10年 | 真兇再現 |
| 趙作海案 | 故意殺人 | 1999.5-2010.12 | 11年 | 亡者歸來 |
| 佘祥林案 | 故意殺人 | 1994.4-2005.4 | 9年 | 亡者歸來 |
| 滕興善案 | 故意殺人 | 1989.1執行死刑2005.6平反 | 16年 | 亡者歸來 |
| 黃亞全、黃圣育案 | 搶劫 | 1993.8-2003.9 | 10年 | 真兇再現 |
| 孫萬剛案 | 故意殺人 | 1996.1-2004.2 | 8年 | 真兇再現 |
| 李久明案 | 故意殺人 | 2002.7-2004.11 | 2年 | 真兇再現 |
| 杜培武安 | 故意殺人 | 1998.4-2000.7 | 2年 | 真兇再現 |
(本圖統計數據參考法律博客)
從上述冤案可以看出,真正是法院自動再審得以糾正的幾乎沒有,糾錯的因素大多在于“真兇再現”或者“亡者歸來”,蒙冤者及其家人的長期申訴信訪,得以引起“兩高”重視,重啟復查予以糾正。現實中,很少有蒙冤者家屬能夠經受時日消磨,耐心伸冤的。對于這些重大冤案來說,通過正常申訴途徑糾正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比如具有較大影響的張氏叔侄、佘祥林、趙作海等正常申訴都未得到平反,直到“真兇再現”或者“亡者歸來”才峰回路轉,出現了“意外”的契機。對于一般的刑事案件想要通過正常申訴得以再審恐怕更是難上加難。
相較于旁觀者來說,正義對被害者才是最重要的,才有存在的意義。對大眾來說,遲到的正義不過是對自己的安慰,安慰我們在法治社會下,但愿不會再遭此喪盡天良的對待。
“正義會遲到,但不會缺席。”最近湖南“操場埋尸案”再次讓“遲到的正義”成為一個熱點話題。隨著部分事實細節公之于眾,在為作案手段殘忍令人震驚,人們對即將到來的正義充滿期待,充滿欣慰,這是人們對正義最樸素的渴望和禮贊,也僅僅是渴望和禮贊。
感性不等于理性。法律上的非正義包括實體的非正義和程序的非正義兩個方面,而我們往往只關注實體,以結果論是非。只有程序的正義才能保證實體的正義,人之為人,在法治國家依法享有的權利不被非法剝奪,這是最起碼的個人尊嚴和國民幸福感,遲到的正義不僅僅在實體上造成了非正義,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程序非正義,所以遲到的正義非正義。
罪刑法定歷來被人稱贊,但是在刑事司法層面罪刑不完全是法定,罪刑在某種意義上是人定。為什么這樣說,罪刑法定是應然層面的,現實情況是罪與非罪的認定和刑罰的裁量都是人定的,只不過裁判者并非為所欲為,而是在依法享有裁判權的同時,法律劃定了裁判者權力的范圍,在法定的空間、幅度內和程序下依法定罪量刑,給權力套上了枷鎖,要求裁判者根據法律規定的條件來認定案件事實,進而認定法律對涉案事實的評價,最終做出判決,但裁判者還有有較大的裁量空間,這是實體上的操作。
自國家、法律等制度產生后,如何讓司法裁判不受外界干擾,一直是中外法治理論永恒而持久的問題。刑法作為公法,涉及對公民的自由乃至生命的限制與剝奪,自由裁量權能否正確適用,至關重要。隨著人們對過往歷史的深度反省,刑法典的修正與完善,刑事自由裁量權也日益受到越來越多的規制。對刑事司法人員自由裁量權到底是采取一種嚴格限制的,抑或保持裁量的相對自由,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刑法適用不僅及于行為及行為所指向的危害結果,還需考察行為背后所反映的行為人之主觀惡性。因此,相對于其他部門法而言,刑法的適用更具有精密性,更關注人本身與人性,刑事自由裁量權有其自身獨特的一面。
首先,刑法是二次制裁法,刑罰涉及對個人重大權益之限制與剝奪,刑罰權的發動是被迫的、不得已的,刑罰適用邊界、方式必須由成文法作出明確規定,意味著刑事自由裁量權必須基于罪刑法定主義下的實體法規則——一套以刑法典為主的刑罰制裁規則。必須指出的是,由于刑事立法采取了違法與刑罰制裁的雙層體系,最高司法機關不斷出臺種種個罪之司法解釋以明確刑罰的具體適用,又基于“同案同判”,推行量刑規范化,均基于量刑均衡、裁判尺度統一的考量。
其二,我國未采取事實判斷與法律判斷二元制模式,而采取一種和大陸法系國家相似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一體化司法裁決模式。刑事司法官不僅僅要對法律適用作出選擇,還必須對事實作出判斷,這說明自由裁量權包含了證據取舍與事實判斷權,也意味著司法判斷交由專業司法官群體。
其三,所謂的“李斯特鴻溝”,即刑事政策被認為是刑法不可逾越的一道鴻溝,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故需要最高司法機關通過頒布規范性文件,以銜接刑事政策與刑罰裁量。
可以看到,中國當下司法對刑事自由裁量權采取一種嚴密的規制體系,規則、制度的設計者目的在于對刑事司法官在證據與事實判斷、入罪標準與量刑尺度的整個裁量過程進行全方位的監督。
刑罰的終極目標是罪刑均衡,同案同判。近年來,立法、司法解釋日益精細化,證據與事實認定規則、實體規則、量刑規則等司法操作規則進一步完善。筆者認為,可以從司法審判過程公正、完善細化刑事法律規則具體內容等方面進行努力,讓刑事司法官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的同時,能夠較好地運用刑事自由裁量權,進而維護審判結果的公正,促進司法正義,提升司法公信。
這里有必要提及一點,所謂的司法三段論:大前提(法律規范)——小前提(案件事實)——結論(裁判結果),這是永遠正確的,但也是永遠沒有應用價值的,言之輕巧為之艱難。刑事司法的精髓在于事實認定而不是法律適用,但就法律適用來說,裁判者的嫻熟程度是有保障的,或者說法律適用的爭議不會特別大,不排除個別案件作為特例的存在。
大多數時候冤假錯案的問題出在事實認定上,司法三段論應該是司法經驗——客觀事實——法律事實。一個有責任心長期從事司法工作的從業者在辦案實踐中積累的提煉事實的經驗是復制不來的,客觀事實準確的說是不成立的,因為誰也不知道客觀事實是什么,最初表現為一起事件,經過法定程序在證據證明的基礎上歸結為法律事實,這一環節非嫻熟的經驗而不可完成,新手上路要當心。
當然,經驗也講求實效,一則是有些經驗是過時的落后的,二則是新人的好奇心和責任心會更強,經驗豐富的人未必事必躬親、面面俱到。法律事實的提煉是案件是否會成為冤假錯案的前提。
細數每一個被糾正的案件,由一種結果改判為另一種結果,這是實現正義嗎?顯然不是,結果本該如此,不是正義遲到,而是裁判者為(他人)曾經錯誤的裁判在贖罪,原本錯誤的裁判產生的惡果會因為改判而恢復嗎?肯定不能,被害者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豈可由裁判的糾正而復原,至于財產損失根本無法計算。
毋庸置疑,應當稱贊糾正冤假錯案的所有參與者,是他們揭露真相,還原真實,給每一顆冰冷的心一絲絲安慰。同時,冤假錯案糾正的越多越更表明曾經的裁判問題越嚴重,原本應為而不為、亂為,錯誤的糾正更多的應該是引起我們的深思和檢討,而不是一路高歌,因為已有的錯誤是糾正不完的,況且不可避免的還可能會出現新的錯誤的裁判,糾正已有的錯誤是分內之責,杜絕當下的錯誤更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程序正義保障實體正義不是一句空話。個案是形形色色的,即便性質相同,所有案件在事實細節和具體情節上都有差異,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更會有差異,在裁判結論作出之前,多多少少都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所以,個案的實體裁判依據的較為抽象的,不可能也不應該具體到細節末節上。裁判結果是看得見的,裁判者達成裁判的過程是看不見的,但是案件的裁判過程應該對當事人、律師透明、公開,讓他看得見、摸的著,程序的明確、具體和可操作就是“看得見的正義”,也就是程序正義。
程序的公開化就要權力受監督,越權有顧慮,讓被告人全方位參與,辯護人全方位參與,保證其法定權利得到行使,而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權利,程序正義能夠保證辯護權的實現,也只有程序正義才能較好的保障辯護權的實現。
從實體與程序的角度講,遲到的正義非正義。不但如此,在刑事司法中,司法裁判講求法定性、準確性,還講求及時性。司法的及時性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不可操之過急,草草定案,二是不得過于遲緩,亡羊補牢,這是背離程序正義的兩種極端。
這種司法裁判的及時性一般有兩個看似矛盾的要求:一是裁判的形成不得過于遲緩,二是司法程序的運作不得過于急速。換言之,及時性講求的是一種典型的“中庸之道”,是在過于遲緩和過于急速之間確定的一種中間狀態。在司法裁判過程中,過慢和過快構成了與程序正義直接背離的兩種極端。
司法程序都是有期間的,暫且不論期間合理與否,法定期間都是要杜絕過快或者過慢的裁判,從追訴犯罪的角度來講,每一起裁判都是罰當其罪、判當其時,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安寧都對及時性具有內在的要求,被告人也需要及時裁判。
要具體界定什么及時性是困難的,但是要說明兩頭的極端表現卻是可以的。過快或者過慢都是相較法定期間內而言的,超出法定期間即為違法。如果一起案件遲遲不出裁判,辦案時間的過度延長,會直接招致案件事實難以查清的困境,證據的流失往往導致案件的事實真相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越來越難以查明,判決結果出現錯誤的幾率在增加。裁判過程的遲緩和低效很可能帶來不公正的裁判結論。
長期羈押而案件未決,對于被告人而言,其人身、財產損害更是無法計算,精神折磨非親歷者不可體會,對于家庭、社會都是損傷,在冤假錯案中也使得真兇逍遙法外,被侵害的法益得不到及時的恢復和補償。
當然司法裁判也不是形成得越快越好。操之過急,其危害不比遲延裁判小。急則亂,亂則易錯。因為急速的裁判則容易簡略應有的裁判程序,被告人的權益會被忽視,這在歷次嚴打中追求從重從快可見一斑。“嚴打”自1983年以來已經開展了多次,縱觀歷次“嚴打”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嚴打”偏差是很容易出現的,如下表:
|
年份 數值 選項 |
嚴打、嚴懲斗爭 |
從重 |
從快 |
依法 |
法制法治 |
刑事審判案件數 |
重點犯罪件數及對應比例 |
|
|
1983 |
1984 |
1521 |
8 |
6 |
21 |
16? |
—— |
—— |
|
1985 |
175 |
3 |
3 |
17 |
7? |
31萬 |
14萬45% |
|
|
1986 |
1613 |
7 |
3 |
30 |
11? |
24.6萬 |
12.5萬51% |
|
|
1996 |
1997 |
3220 |
4 |
3 |
38 |
71 |
57萬 |
—— – |
|
2001 |
2002 |
143 |
1 |
1 |
30 |
54 |
73萬 |
36萬49% |
|
2003 |
102 |
0 |
0 |
27 |
61 |
—— |
—— |
|
|
2004 |
2005 |
101 |
0 |
0 |
42 |
11 |
64.4萬 |
26.6萬41% |
|
2010 |
2011 |
72 |
0 |
0 |
30 |
32 |
78萬 |
29.2萬37% |
|
2014 |
2015 |
153 |
0 |
0 |
36 |
413 |
102.3萬 |
39.8萬39% |
這是歷次“嚴打”中刑事案件的統計情況。由此可見,專項行動的針對重點罪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進行,地方辦案機關往往基于政績考量,將其作為政治任務來完成,批量抓人、聲勢浩大,比如之前公開報道的各省份在開展“掃黑除惡”專項行動后迅速抓捕了嫌疑犯數以千計,比如山西省公安機關共打掉涉黑涉惡犯罪組織和團伙54個,其中打掉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4個,打掉惡勢力犯罪組織50個;陜西省公安廳1月25日起在全省公安機關部署開展掃黑除惡集中收網行動以來,警方已打掉黑惡團伙202個,抓獲黑惡犯罪涉案人員1426名,破獲黑惡犯罪案件532起,查封、凍結、扣押涉案資產921萬余元;河南省首批“掃黑除惡”抓捕1482人;浙江首批“掃黑除惡”抓獲1200人等等。運動式行動昭然若是,一味強調從快從重不可避免的會出現“嚴打”偏差,侵犯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我們要深知:犯罪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也是社會發展中必然存在的現象,是很難通過一次“嚴打”就能完成的,盤根錯節、利益交織的疑難問題更是如此。因此,運動化執法傾向早該杜絕,依法行使裁判權,保障各方的合法權益是大勢所趨。
畢竟,程序正義的維護是需要有一定的時間加以保證的。沒有必要的時間投入,被告人、被害人及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在調查證據、準備防御和有效影響裁判結論方面,就很難有所作為。沒有必要的時間保證,訴訟各方在法庭上也難以展開充分的舉證、質證和辯論,使得法庭審判往往因此而流于形式,裁判的公正也無法保證。
簡言之,裁判不能過于急速,也不可過于遲緩,兩者都會走向程序上的非正義,都會導致冤假錯案的出現和正義的缺席。
冤假錯案的糾正是及其困難的。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有權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申訴的權利,同時規定人民檢察院發現確有錯誤的裁判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人民法院發現確有錯誤的裁判可以決定再審。檢察院和法院是平反冤案的職能部門,各級法院、檢察院都設立有刑事申訴審查部門,從事冤案審查。但是,是主動審查還是被動審查,我們不得而知,糾正冤假錯案異常困難卻是現實。
司法實踐中,既然法律明確規定再審糾錯程序,為什么這些冤案不能通過正常的申訴途徑來解決呢?從制度上說,我國刑事再審程序的啟動,事實上只以生效判決確有錯誤為前提,這有很明顯的主觀主義色彩;從程序上說,一般由司法機關通過書面審查啟動,沒有當事人、律師、證人直接參與的聽證程序。哪些新證據能證明原審判決確有錯誤,由司法機關,甚至是由原審法院來認定,這就增加了翻案的難度。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份判決,但是案件的辦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參與人員廣泛,經歷程序復雜,僅從一個結果來判斷整個過程的錯誤顯然是具有較大困難的,糾正冤假錯案也就變得艱難。
對冤假錯案的強力糾正,是我們孜孜不倦的祈求,一些已經成為“歷史”的案件被重新翻出,辦案機關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糾正冤假錯案,只是這樣的案例太過罕見。面對現狀,糾正冤假錯案的路在何方,當前從最高人民法院自上而下要求糾正冤假錯案的現實情勢下,盡管荊棘蹣跚,也是難得的時機,以糾正冤假錯案為契機,保障被告人的各項法定權利,保障辯護人依法行使法定權利,最大可能的防止出現冤假錯案,是司法從業者最崇高的使命。因為遲到的正義非正義,與其事后糾錯,不如事前防范避免出錯。
當然,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